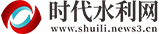编者按:
《丘中有麻》历来论者多以为是情诗,或者以为是思贤之作,白军君先生说,都不是,它就是一封家书,是诗作者安排家中事务而已。这个解读,的确前无古人,即便是编者,也是大感讶异。不过,对《诗经》的解读,本来就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只要能自圆其说,却也不能说就是错了。军君兄所以能独树一帜者,正为其能不落前人之窠臼也。
废话休说,且看白军君先生如何阐释《丘中有麻》,相信读者自有好恶、论断。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历代学者对《诗经·王风·丘中有麻》给出过自己的释译,他们的解说差异巨大,有说是写私奔的,有说是招贤偕隐的,也有说是思贤之作的,还有说是写情人定情过程。粗略统计,在文学史上留下记录的至少有七种之多。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依我看,就是历代大儒想多了,过度引申诠释。
《风》诗是什么?它就是一部色彩斑驳的野史,更多的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饮食男女,风情万种,摇曳生姿才构成它最主要的文学风景。后世一些文人硬要把经国大事往它“身上”套,妄图把《风》诗引向雅致的歧途。如此一来,丰饶生动的《风》诗变得艰涩干瘪,原本鲜活的文字变得僵硬。
读《诗经》,我们首先须心里有底,这个底就是,内容绝对不会触碰到“淫”,即便今天的人们读到情感“出格”的地方,那也是时代变迁使然。《诗》经历了周宣王和平王东迁后两次编订,官家的介入,自然是托底的,这个底就是作品内容“干净”,用以教化万民。孔子是第三次修订。
孔子是什么人呢?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不要忘记,孔子还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周游列国,大半生劳碌,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68岁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担任《诗》的主编,他试图通过订正诗句、“乐正”,从文学文化入手,制止体制和礼法的混乱。这里面包藏着孔子一个巨大的野心,他在做政治文化民心工程。我说这些常识,只想说明,所谓“淫”诗,在《诗经》中绝不可能存在。孔子不会干这个事情。我相信孔子的纯粹,审美,还有他对情感表达的尺度的把握。
来,我们进入文本: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先从总体上把握。
《丘中有麻》写到三种农作物:麻、麦、李;写到三个人:子嗟、子国、之子;同一个及物动词“留”使用了三次。还有吗?当然,还有一个“将”,千万不可放过和轻视这个“将”字,这个“将”字看上去出现了两次,实际上第三章也有,它就隐藏在“贻我佩玖”里头。只不过,它同时给出了原因——她还曾赠我佩玖。在《丘中有麻》这首诗中,这个“将”字太重要了,它虽然只是表示柔婉的语气词,包含着客气的意韵,但是,它起到统领整篇作品的口吻作用。结合把“麻”“麦”“李”两种重要的农作物和一种水果“李”留给他人这一诗歌的主要叙事,我们不难断定,《丘中有麻》是一个男子的口吻在叙说家务,因为当时是男权社会,又处在完全的农耕时代,处置粮食和经济作物这样的家庭大事绝对不会由一个处于家庭配角的女性来做主。
全诗三章,都采用“丘中有某,彼留某某”的句式,这是《风》诗中常见的兴体表现手法,三个兴句中,“丘”没有生成意象,丘中之“麻”“麦”“李”与动词“有”结合而成存在事象,而绝无意象。同样,最后一句“赠我佩玖”中的“佩玖”也是一种实体性的事象描述。
意象有它的内涵和生成机制,不是每一首诗歌中都有。意象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不同的语象组成具有诗意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才能产生兴发的功能,生成独特的意象。
“丘”是一个空洞的形状概念,“有麻”“有麦”“有李”都是对“丘”作出的具体的场景描绘,使“丘”的地理位置最终确定了下来。
我们再来考察诗中的“佩玖”。《诗经》中,《木瓜》篇写到“琼玖”,《女曰鸡鸣》篇中写到“杂佩”,和《丘中有麻》篇中的“佩玖”其实就是一种东西,玉佩。古代,只有女子赠送男人玉佩。这个非常明确。《礼记·玉藻》中这样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言念君子,其温如玉。”孔子认为玉具十一德,因“君子比德如玉”的观念深入人心,君子佩玉成为一种时尚。直到成书于乾隆时期的《红楼梦》,男主人贾宝玉仍旧脖子上戴着玉。
“子嗟”“子国”是人名,“之子”不是人名,是“那个人”。“之子”一词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如《有狐》“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桃夭》“之子于归,宜室宜家”等。“之子”连用,“之”字多为指示性代词,有明确的指向性,译为“这”,“子”在古代是男女的通称。“将其来施”中的“施”,与《葛覃》篇“施于中谷”、《兔罝》篇“施于中逵”、《頍弁》篇“施于松柏”之“施”语义一样,都是罝的意思。
解决了诗作文本中词语的训释,事情变得相对简单了起来,诗旨变得明媚,清晰。我试译如下:
山坡上面种的麻,
把它留给子嗟吧。
把它留给子嗟吧,
请他帮忙来处置。
山坡上面种的麦,
把它留给子国吧。
把它留给子国吧,
请他收割自己吃。
山坡上面李子树,
把它留给那女人。
把它留给那女人,
她曾赠给我佩玖。
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彼留”就用了两句,占据了一半篇幅,意在强调交代、嘱咐的内容和对象。如果我的释译可备一说,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我还要说,这首《丘中有麻》是一位远离家乡的游子在外做事,而且安身牢固,写给家乡故交的一封家书,写信的人在家乡没有了什么亲人,而且这封信写在暮春。这样一种判断,考虑到了古代的邮路不畅。也或许,是捎的口信,后来被人编成民歌。把日常生活,家书改编为歌曲传唱,是古人对生活诗意化的表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坐实了孔子编订《诗经》努力恢复周礼的雄心壮气。孔老师认为,周朝的人民过着一种有秩序的浪漫的诗意化生活。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思潮和创作方法,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形成系统理论,《诗经》早就运用自如了。
《丘中有麻》在手法上开门见山,但这种写作手法丝毫不影响它成为《诗经》中的名篇,除了它把家书写成诗这个特点外,它其实写的很“圆”,这个“圆”指的是作品的完成度很高,诗歌在两个叙事层面展开。作为非虚构作品,《王风》来源于河南郑州及周边地区,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收麦在5月中旬,割麻在7月下旬,摘李在7月。所以,我说这封家书必须在暮春抵达收信人手里,或者把话捎给当事人。否则,麦子会烂到地里面。这是明面上的叙事。另一层面的叙事是隐语,通过钩沉完成。“贻我佩玖”那个曾经赠我玉佩的人。那个人呢?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心知肚明。“子嗟”“子国”都在直呼其名,唯有“之子”隐其名姓,可见,“之子”应该已经成家,而且就嫁在了本村。
在钩沉层面,隐含了诗人和子嗟的交情,和子国的友情,更多的是和之子的恋情。
我还想说,《丘中有麻》虽然是短制,但是,它和西方文学中的《圣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王朝早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一样伟大,诗人们深知,人类所经历、感知的生命、生活形式和经验,是人类培植写作的真实和根土。换句话说,写作是可以从生活经验出发的。
好的诗歌具有开阔的空间。一句“贻我佩玖”写出了千山万水的人生往事,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为《丘中有麻》的审美增添了无穷的含蓄蕴藉……